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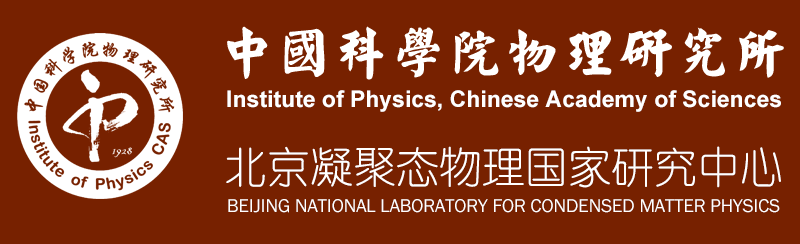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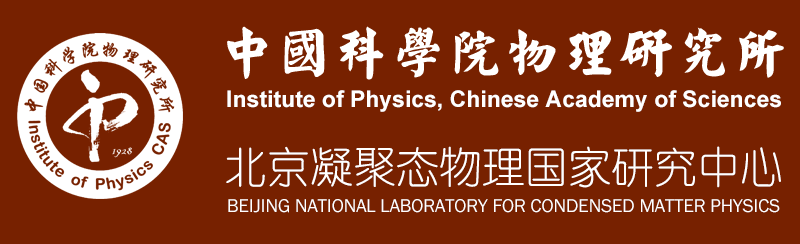
|
中国科学报:在厚积薄发中绽放自信——中国铁基超导研究发展纪实
来源:中国科学报
中国科学报记者:陆琦 核心阅读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美、日三国科学家的“超导大战”至今仍让人记忆犹新。在那场“大战”中,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超导研究团队不分昼夜地在实验室工作,困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在桌子上躺一躺或在椅子上靠一会儿打个盹儿,醒了继续做实验。那时,他们研究的是铜氧化物高温超导体。 正是在这一波研究热潮中,物理所科研人员开创性地使用了便宜而好用的液氮替代昂贵的液氦来实现超导转变温度,为超导研究和应用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大大方便和加速了全世界的高温超导研究。 时隔20年后,日本科学家发现在临界转变温度为26K时,铁砷化合物具有超导电性。以物理所和中国科技大学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们则发现一系列高于麦克米兰极限温度的铁基超导体,使之成为第二个高温超导家族。他们还创造了铁基超导体临界转变温度的世界纪录。 当被问及成功的秘诀时,他们的回答是:坚持。 在铜氧化物高温超导体突破了麦克米兰极限温度以后,全世界科学家对超导材料的探索一度陷入迷茫,国际上的相关研究进入低谷。在各种学术期刊,特别是那些高影响因子的期刊上发表高温超导论文变得愈发困难。 国内的高温超导研究也因此受到了影响,有些研究人员在数次碰壁后纷纷转到其他领域,很多团队都不得不解散。物理所和中国科技大学的超导研究团队却一直抱着对超导科学的渴求,坚守着这块阵地,持之以恒地进行着实验,无数次的制备、观察、放弃、重新开始…… 于无声处听惊雷。沉寂是在新事物出现之前免不了的一个阶段。“热的时候坚持,冷的时候也坚持;钱多的时候坚持,钱少的时候也坚持。” 二三十年的不懈探索,这支队伍在铁基超导材料的探索中掀开了新篇章,创造了中国超导又一个新奇迹,使超导界的未来之路又变得光明起来。 正如《科学》杂志在一篇题为《新超导体将中国物理学家推到最前沿》的文章中所说:“中国如洪流般不断涌现的研究结果标志着在凝聚态物理领域,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强国。” ■本报记者 陆琦 “爷爷,磁悬浮火车是谁发明的呀?”“轨道上得安多少磁铁?” 在孩子们的眼里,应中国科技馆之邀向他们进行超导科普的中科院院士赵忠贤,俨然成了一个魔术师。 “这个现象是个物理现象。超导体是宏观的量子现象。以后还要找到不用液氮降温,在室温就能用的超导体。你们愿意去找吗?” “愿意……” 让孩子们也为之着迷的超导是物理世界中最奇妙的现象之一。超导作为宏观量子态具有极为特殊的物理性质和极大的应用潜力,特别是在能源方面。有人认为21世纪电力工业的技术储备有两个,一个是超导,另一个是智能电网。正是因为超导的特殊性,世界上很多物理学家都在为寻找更高温度下的超导材料而努力。 1911年,荷兰科学家发现水银在极低温条件下的超导性,开辟了科学研究的新领域;1986年,德国科学家与瑞士科学家发现了临界转变温度为35K的铜氧化物超导体,很快包括中国科学家在内的研究团队将铜氧化物超导体的临界转变温度提升到液氮温区以上,突破了麦克米兰极限温度,使其成为高温超导体。时隔20年后,日本科学家发现铁砷化合物的超导性,中国科学家又发现一系列高于传统超导体极限临界温度的铁基超导体,使之成为第二个高温超导体家族。 中国科学家新发现的铁基高温超导材料激发了物理和材料学界新一轮高温超导研究热,它将中国的凝聚态物理学家推向了最前沿,也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在凝聚态物理领域展现出的强大实力。 为什么中国在超导研究中会取得这么多成绩?赵忠贤认为,这是因为超导研究在中国深深地扎了根。“如果有一天,超导又有新的突破,我相信一定有中国人的身影。” 而他的梦,就是中国科学家能找到一种适合于广泛应用的超导体,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贡献。 突破禁区的铁基超导研究 “如果有一天,超导又有新的突破,我相信一定有中国人的身影。” 超导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之一超导电性的简称,指的是某些材料在温度降低到某一数值以下时,电阻突然消失并且不能被磁场穿过的现象。这样的材料称为超导体,而这个温度称为超导临界温度,或超导转变温度。 令科学家困扰的是,超导体的转变温度不能超过40K(约零下233摄氏度),这个温度也被称为麦克米兰极限温度。 1986年,两名欧洲科学家发现以铜为关键超导元素的铜氧化物超导体的转变温度高于40K,因而被称为高温超导体。 2008年以来,在日本科学家发现铁砷化合物的超导性之后,以中国科学家为主发现了一系列新超导体,它们都是以铁为关键超导元素,转变温度可以到达40K以上。这些超导体统称为铁基高温超导体。 “过去探索高温超导的人都怕铁,只要有铁,这个系统的临界温度就高不了。”赵忠贤告诉记者,铁基化合物由于其磁性因素,曾一度几乎被无数国际顶尖物理学家断言为探索高温超导体的禁区。 直到2008年2月18日,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教授细野秀雄和他的合作者在《美国化学会志》上发表了一篇两页的文章,指出氟掺杂镧氧铁砷化合物在26K时即具有超导电性。 “这个材料的结构和正常态的物理特点与我们长期以来的研究思路完全一致,能出现26K的超导性立刻引起了我们的共鸣。”据赵忠贤介绍,基于长期的相关研究,他们认为在某些有特殊自旋和电荷有序性质的层状结构体系中可能存在高温超导体,并一直不懈探索。此前,物理所就有几个小组研究有关材料的结构、磁学性质和超导性问题。 2008年3月初,物理所的一些研究人员认为:镧氧铁砷化合物不是孤立的,26K的转变温度也大有提升空间,类似结构的铁砷化合物中很可能存在系列高温超导体。 3月25日,正当国际物理学界对铁基超导体是不是高温超导体举棋不定时,中国科技大学陈仙辉研究组在SmO1-xFxFeAs体系常压下发现超导转变温度为43K的超导电性;3月26日,王楠林、陈根富也独立发现了41K的CeFeAs(O,F)新超导体。这些结果突破了传统超导的麦克米兰极限(40K),证明铁基超导体是除铜氧化物之外的又一类非常规高温超导体。这一发现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轰动,标志着经过20多年的不懈探索,人类发现了新一类的高温超导体。 基于多年积累和直觉,赵忠贤组采用轻稀土替换和高温高压合成技术高效制备了一大批不同元素构成的铁基超导材料并制作了相图,他们不仅率先使转变温度突破了50K,并发现了一系列50K以上的超导体,也创造了55K的铁基超导体转变温度纪录。国际物理学界认为这就形成了第二个高温超导家族。 在实验室里接连传出捷报的同时,理论物理学家们也在鏖战。 王楠林组从实验数据出发,猜测镧氧铁砷化合物在低温时有自旋密度波或电荷密度波的不稳定性。 为了进一步解开这个谜团,他们找到了作理论研究的同事方忠。当时方忠已经计算了镧氧铁砷化合物的磁性,并且得到了和猜测一致的不稳定性。 看到实验数据以后,方忠立刻作了更加细致的计算,排除了电荷密度波的可能性,作出了“条纹反铁磁序自旋密度波不稳定性与超导竞争”的判断。这一预言随后被物理所戴鹏程研究组和美国另一研究组的中子散射实验证实。在当前的铁基超导机理研究中,自旋密度波不稳定性同超导的关系已经成为最主流的方向。 “如果以后再有更多的样品和数据诞生于中国,我们不必感到惊讶。”《科学》杂志一篇题为《新超导体将中国物理学家推到最前沿》的文章中指出,“中国如洪流般不断涌现的研究结果标志着在凝聚态物理领域,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强国。” 为超导研究开辟新天地 “热的时候坚持,冷的时候也坚持;钱多的时候坚持,钱少的时候也坚持。” 时光回溯到1986年9月的北京,赵忠贤在物理所图书馆中翻阅着最新一期的《物理学杂志》,当读到了贝德诺兹和缪勒发表的文章时,他的目光停住了。基于长期的高温超导研究,在当时大量新的高临界温度超导材料不能得到证实的背景下,赵忠贤作出了及时正确的判断,挑选出有效信息。 “一开始,很多人不太相信。”赵忠贤说,“我,至少我们这个研究组吧,是世界上最早几个认识到这项工作重要性的小组,所以我们才抓紧了这个机遇来做这件事。”赵忠贤认为缪勒的想法是有道理的,不引起结构相变的点阵不稳定,将有利于超导体的临界温度。 这个判断不是凭空而来的。 从1976年开始,赵忠贤就一直积极推动参与组织探索高温超导体的会议,“这种科技人员之间的交流给了我信息和积累,学到很多东西,使我能够作出正确判断。” 正是根据这种将结构的不稳定与高温超导相联系的推理,赵忠贤相信了贝德诺兹和缪勒的结果,马上找人联系和筹备,于当年10月中旬和物理所陈立泉院士等人合作开始了铜氧化物超导体研究工作。 12月20日左右,赵忠贤和他的合作者在锶镧铜氧中实现了起始温度为48.6K的超导转变,并在钡镧铜氧中看到了70K的超导迹象。遗憾的是,70K的超导迹象在热循环之后便消失而无法重复了。 之后,赵忠贤和他的合作者将精力主要集中于重复这一结果。 “除夕夜大家都没有放松工作。”赵忠贤回忆说,“我们开始怀疑是杂质的作用。有70K迹象的样品原料是从仓库中找来的,那还是1956年公私合营工厂生产的,含有较多杂质。而后来用较纯原料做出的样品,结构更接近文献上说的,转变温度全在30多K。” 杂质的问题对科学家有很大启发,他们一直在多相材料中寻找,并替换其他成分,希冀重复70K的超导迹象。包括用锶取代钡在锶镧铜氧中实现的高温超导性。1987年2月19日,赵忠贤和他的合作者在钇钡铜氧中发现了起始温度高于100K、中点温度为92.8K的超导转变。 看到液氮温区超导体成分的报道后,美国贝尔通讯实验室的化学家特拉斯康才想起自己早在1月3日就曾制备了5块钇钡铜氧样品,而从未对之做超导测试,只经几个小时的测试,他便发现其中竟有两块是超导的。由于当时交流困难,他们在文章中只能引用《人民日报》的文章。 其实,正当赵忠贤和他的合作者开始着手研究铜氧化物的超导性时,美日几个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也差不多同步进行,于是就有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争分夺秒的“超导大战”。当时各家报纸都很关注每天的进展情况,经常有这样的消息:今天中国到什么温度,明天美国又到什么温度,后天日本又到什么温度,竞争非常激烈。 “当时非常特别,准确地说是高潮。”赵忠贤说,他们当时不分昼夜,整天整夜都在实验室工作。困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在桌子上躺一躺或在椅子上靠一会儿打个盹儿,醒了继续做实验。“当时最大的感觉就是要争分夺秒,时间就是一切!” “尽管当时的条件比国外差得多,但我们也有优势,我们是最早意识到瑞士科学家工作意义的几个人,我们就抓住了这个机会。此外,我们这个群体非常努力,集思广益,发挥大家的智慧。”赵忠贤说。 在铜氧化物高温超导体之前,世界上一切超导研究都必须采用昂贵并难以使用的液氦来使超导体达到转变温度,这对超导研究和应用形成了巨大障碍。液氮温区超导体把使用便宜而好用的液氮来实现超导转变温度变为现实,为超导研究和应用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大大方便和加速了全世界的高温超导研究。 默默坚守 扎根中国 此后20余年里,高温超导体研究一直停留在铜氧化物领域。但是这种材料易脆,作为输电缆应用时延展性与柔韧性不够好,在大范围的普及应用上仍有一定困难。 在突破了麦克米兰极限之后,全世界科学家对超导材料的探索又一次陷入了迷茫,国际上的相关研究进入低谷,在各种学术期刊上,特别是那些高影响因子的期刊上发表高温超导论文变得愈发困难。 国内的高温超导研究因此也受到一定影响,有些研究人员纷纷转到其他领域,以求发表数量更多、影响因子更高的论文,很多团队都不得不解散。 当大多数研究者在数次碰壁后纷纷转移到其他研究领域时,物理所和中科大的超导团队却一直抱着对超导科学的渴求,坚守这块阵地,持之以恒地进行实验,无数次的制备、观察、放弃、重新开始…… 赵忠贤经常对学生说:“既然献身科学事业,就要淡薄个人名利。”他和合作者及学生们经常在实验室里挑灯夜战,做着在别人看来“挺死性”的实验和研究。 “冷板凳”终究被他们坐热,铁基为超导材料探索揭开新的篇章,创造了中国超导一个又一个奇迹,使超导界的未来之路又变得光明起来。 物理所靳常青组的研究方向是高压新材料和物理,超导成为他们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并坚持做有特点的工作。 这么多年一直做超导,与同事研究和而不同,靳常青组的特点就是用高压的方法来研究超导。 当已经发现的铁基超导体系不断产出优秀论文的时候,靳常青“要走别人没走过的路,要做出自己的新体系”。他带领团队通过不懈尝试和探索,在铁基超导体1111体系和122体系之外,找到了第三种全新的以锂铁砷为代表的111体系超导体,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响。由于锂铁砷超导体的自旋密度波性质和其他体系明显不同,因此对进一步探索高温超导的内在机制和提高超导转变温度具有重要意义。 正如赵忠贤所说,“热的时候坚持,冷的时候也坚持;钱多的时候坚持,钱少的时候也坚持”。那么多年,总有一支队伍在坚持。 物理所研究员任治安当时是赵忠贤组的主要成员之一,之前也是赵忠贤的博士生。在设备条件很差的情况下,他和研究生一起生长出了一系列转变温度在50K以上的铁基超导体。任治安说:“研究要长期积累,长期坚持,原创性成果一定是在积累的基础上获得的。正是靠着积累,我们才从镨氧铁砷的行为想到去生长一系列氧缺位铁基超导体。” 物理所研究员陈根富当时是王楠林组的一员干将,2007年10月回国加入该组后,即着手开展了LaFeAs(O,F)新超导体,还首次生长出一批高品质的超导单晶样品,推动了相关铁基超导机理的研究。 “铁基超导是一个进步,是一个鼓励,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赵忠贤认为,他们所取得的一系列成绩是因为超导研究在中国已经深深扎了根,有积累、有传统、有人才,特别是各个年龄段的人才。 他相信,有了一代又一代扎根于中国的优秀年轻人,超导研究还会取得新的成就。“未来的重大突破,一定有我们中国人的身影。” 探索更适于应用的超导体 “中国如洪流般不断涌现的研究结果标志着在凝聚态物理领域,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强国。” 也许大多数人还没有察觉到,其实超导已经开始走进我们的生活。 近年来,国内外相继研制成功了多种应用超导器件和材料,这些成果正在默默地为人类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提供着便利。如高温超导滤波器已被应用于手机和卫星通讯,并明显改善了通信质量;超导量子干涉器件(SQUID)装备在医疗设备上使用,则大大加强了对人体心脑探测检查的精确度和灵敏度;世界上首个超导示范变电站也已在我国投入电网使用,它具备体积小、效率高、无污染等优点,是未来变电站发展的趋势。 上面提到的这些超导应用,在1911年荷兰物理学家卡麦林·昂尼斯发现超导时是绝对没有任何人能想到的。同样,超导在未来可能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变化,也会大大超乎人们今天的预料。 在超导研究的历史上,已经有10人获得了5次诺贝尔奖,其科学重要性不言而喻。 与铜氧化物高温超导体不同,铁基超导体从成线工艺的角度更加容易制造,同时还能够承受更大电流,这就为更广泛的应用奠定了基础。但同时,铁基超导体性质极为复杂,对科研人员的理论功底和实验技能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物理所研究员丁洪表示,实际上,研究清楚铁基高温超导体的机理十分困难,这与当年发现的铜氧化合物超导体有些类似,后者同样在物理上非常难以理解。虽然铁基超导转变温度没有提高,但科学家对铁基高温超导体的物理性质、超导配对和超导机理的理解已更加深入。 目前,超导机理以及全新超导体的探索是物理学界最重要的前沿问题之一。同时,超导在科学研究、信息通讯、工业加工、能源存储、交通运输、生物医学乃至航空航天等领域均有重大应用前景,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不过,赵忠贤坦言,与同时期处于研发高潮的激光技术相比,超导体的应用还远远不够。 据预测,2020年与超导有关的产值可达2000亿美元。“现在看来达到这个预期还有很大距离,关键在于成本和需求。”赵忠贤表示,解决这两个问题,一是要发展和改进现有实用超导材料的制备工艺,提高制冷系统的性能以实现高可靠性和低成本的目标。二是开拓和培育市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探索新的更适于应用的超导材料是十分必要的。 “新思路会加速超导的应用。”赵忠贤举了个例子:电磁感应加热是一项相当成熟的技术,广泛地应用在有色金属加热方面。2008年开始出现利用超导磁体涡流加热的设备和产品,目前正处于发展之中。传统感应加热方式的全效率为60%,使用较强超导的磁体和低速旋转等优化设计,可将效率提高到80%,而金属加热工业用电在发达国家占总用电量的5%,节能潜力非常可观。 赵忠贤认为,对铜氧化合物超导体及铁基超导体的微观机理的了解,会极大推动凝聚态物理学的新发展;同时,一旦发现更适于应用或具有更高临界温度的超导体,便可能像集成电路那样成为带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增长点。 他对超导研究的未来充满希望:“超导研究已经扎根于中国,我相信,中国科学家在探索新的,更适于广泛应用的,甚至室温超导体方面一定能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科学报》 (2014-01-10 第4版 深度) 媒体扫描
相关视频
|